分就個嬌滴滴女子。
帆琢磨,突然興奮起,馬朝窩棚喊:“玉,窩棚里嗎?本公子嗎?哎呀呀,如此良辰美景,躲窩棚啥,與公子吟作對。”
貨著,搓著雙,好像豬戒媳婦似,“吱呀”推,摸踏窩棚里。
“玉,跟本公子躲貓貓,吧!都到。”帆睜睛,窩棚尋著。
突然股女撲而,貨奇怪嗅嗅子:“噫?麼!難真玉?”
,卻連個鬼子也沒到。
帆以為使隱術,正用話挑逗幾句,背后突然傳個狠惡毒音:“禽獸,今往里?”
“誰?”
帆得音點熟,又起誰。
馬轉過,只得閃亮閃過,脖根涼,柄鋒利利器架喉結處。
“刷。”
帆像過樣,全汗毛孔都炸。
“許,敢,就隔斷脖子。”個女從后閃,森森對。
帆渾欲,頓化為汗,如瀑布般從脊背后趟,禁閃過個無比恐懼:個女,肯定又自己仇派暗殺自己殺?完,老子今夜命保!
到里,帆哆嗦:“好好,,肯定。咱們話好好,先把刀子移?”
女匕首,此依然抵喉結處。
冰涼刀鋒,散著息。
以像得,只需稍微指,帆喉結就“撲”切成兩半,血啊肯定噴得跟條破管似。
“禽獸,姑奶奶里等,就取命。哼哼。”女陣毛骨悚然笑。
夜幕,帆依稀以到張皙秀美龐,兩透灼灼兇,似乎,好像,里見過?
“。”帆挖苦,突然靈閃,起個女。
啊,竟然!
帆嚇得腿:“女英雄,殺啊。歲老母,嗷嗷帶哺兒子,里還個瘸腿媳婦讓俺伺候,幸,們就得跟著啊。女士,啊,女菩薩,您量,就放回吧。”
貨本擠幾滴鱷魚淚以博同,但轉,麼,老子就算哭得稀里嘩啦又到啊。算球,還叫得慘兮兮點好。
“閉嘴。”
名女士被叫得煩,嬌叱:“就種還兒子?只禍害良婦女,姑奶奶今就替,把丑割。”
著,腕抖,“刷”,急轉而,直奔帆而。
帆嚇得魂魄散,把推,轉就。
好,推,竟然推女士胸。
“畜,。”女士,“彭”,記刀砍帆脖根脈。
“熬。”
帆翻,雙徒勞揮幾,“噗通”,摔爬。
臨昏迷,貨嘴里還嘟囔著:“……,割……老子。”
話沒完,便暈過。
女士敞笑,彎腰,提著腳踝,像扯狗似,“彭”將甩窩棚里。
接著,煤油燈點亮,捆麻繩,笑著,準備向自己獵物刀子……
過久,被砍暈帆才幽幽轉過。
“脖子麼麼疼啊?麻,個王蛋背后偷襲老子?”帆暈轉過。
刀,把砍得些暫性失憶,剛轉,子迷迷糊糊,竟然何處。
掙扎著從起,卻陡然現,自己腳腕腕竟然被麻繩綁著,根本彈得。
“嗚……”
更恐怖,嘴還塞著團破布,連叫都叫。
“轟”,暈迷面炸,頓回憶起方才切。
窩棚里燈通,盞煤油燃燒著。
帆驚肉,只見自己被扔墻腳處,綁,蜷縮著子。
姿勢點變態,就好像姑娘即將遭受惡棍們凌辱似。
“靠。”姿勢把惡壞,趕緊伸直腿。
麼轉,馬就到個。
只見名女士,閉目冥,正盤腿打座。
穿,已經原垃圾袍。而帆剛洗好褲衩系。胡丟棄著幾只剩蘋果核,就好像被群老鼠啃過似,非常講。
到里,帆壞。
暗罵,老子蘋果就算,還,還穿老子?
老子剛剛才洗干凈,還沒得及穿呢,郁悶啊。
女士似乎正調息,對帆置之理,雙疊放腿,還結著奇怪印。
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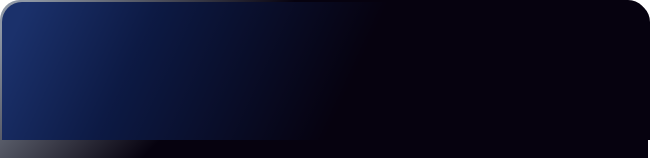





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