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最窮的那年,我掰彎了男主,將自己賣給他。 傅景行因為雙腿殘疾,性格陰郁自卑,最喜歡在床上折磨人。 在女主出現后,我才發現原來傅景行還有這麼溫柔的一面。 為了將劇情拖回正軌。 我在撈夠錢后,留下張字條跑路: 【你個瘸子根本滿足不了我!】 幾經周轉,我逃到了離他最遠的城市。 卻在某天回家時,被人從背后抵在墻上,掌住了腰。 害怕被捅刀子,我嚇得不停求饒。 耳邊傳來傅景行懶散的笑: 「寶貝兒,背后捅死你的,可不一定是刀子。」


十八歲陳決攔住我。 「你剛在畫我,你對我一見鍾情了。」 十九歲陳決說。 「你等我,我會回紐約找你。」 二十歲,陳決在手機上發消息告訴我。 「陳意,我不回來了,你不用等我。」 我在北京找了他十年。 那個年少成名、意氣風發被叫天才的陳決。 高喊同性戀無罪,驚豔我青春的陳決。 端著潑灑被退單的外賣,嚥下了一把五彩繽紛的藥。 他指節上還留著戒痕,是我設計的那枚。 他說:「陳意,你回去吧,我要結婚了。」


最近總是失眠,我心情煩躁。 好兄弟知道後建議我領養一隻成年雄性魅魔。 他說,活幹累了就想睡了。 我不明所以,但聽勸。 第二天就去了魅魔收容所。 但還沒進門,腳腕就被一隻骨節分明的手攥住了。 「哥哥,身上真的好疼,我不想再待在這裡了,能帶我回家嗎?」 渾身是傷的魅魔哭得抽抽噎噎,桃心尾巴不安地蜷在身👇。 「都怪我不討人喜歡,可我也真的不想這樣啊。」 語畢,一顆晶瑩剔透的淚水不偏不倚地掛在了他長長的睫毛上。 看著委屈巴巴的魅魔,我承認自己心疼了。 鬼使神差地把他帶回了家。 直到後來收容所發來提示簡訊。 【領養人您好,由于您領養的魅魔有多次打架鬥毆的前科,特保留您一個月的反悔期,只要您想,一個月內隨時都可以退回。】 我才知道自己領養的魅魔還有兩副面孔。


與一隻佔有慾極強、偽裝成人類的怪物談戀愛是什麼體驗? 謝邀,人在怪談副本,剛喂完觸手。 體驗就是,你得擁有比他更瘋的精神狀態。 此刻,安全屋外是百鬼夜行,屋內是各懷鬼胎的隊友。 而我的男朋友祁宴,正瑟縮在我懷裡,裝出一副被嚇壞了的小白兔模樣。 「阿野,外面好可怕,那個怪物的牙齒有這麼——長。」 他一邊說著,一邊把臉埋進我的頸窩。 與此同時,幾根觸手正沿著我的褲腿向上攀爬。 「好餓……老婆……這幾個人類聞起來好香……」 「我可以吃掉那個寸頭男嗎?就吃一條腿。」 我按住他在我衣服裡作亂的手。 「乖,再忍十分鐘,全是你的。」


我是名滿京城的男花魁。 宰相周庭頌曾為了買下我的一夜,豪擲三千兩。 後來,彥國滅了。 我再次遇見周庭頌,他瞎了雙眼,衣不蔽體地被人牙子關在下等貨的鐵籠裡。 「公子,要看看嗎?三兩銀子一個,您隨便挑!」


喜歡小叔的第三年。 我趁他易感期,偷偷闖進了他的臥室。 一夜荒唐,我一個 Alpha 卻懷孕了。 我想生下這個孩子。 可躲了他三個月,還是被他抓了回去。 醫院裡,商臨洲摸著我微凸的小腹。 雙眼猩紅,步步緊逼。 「哪個畜生把你一個 Alpha 弄懷孕的? 「勁挺大的啊。」


我是 ABO 中的糊咖 Beta。跟醉酒的頂流荒唐一夜,意外懷孕。為了不被封殺,我連夜跑路。頂流找到我時,我正受邀參加娃綜。 頂流氣急敗壞地將我抵在墻上質問:「離婚?單身?我怎麼不記得你曾經給過我名分?」 他的信息素外泄,擾得工作人員戰戰兢兢。 我輕描淡寫地拂開他的手,抱起年年,淡聲抬眸:「陸先生,請收斂一點,你讓我的孩子受驚了。」 他氣笑了,好整以暇地往鏡頭前一坐: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,年年是我們的孩子。」 看著如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兩人。 觀眾炸了。


我和許祁信息素匹配率高達85,但他很討厭我。 當和他匹配率達到95的人出現后,我自覺地離開了。 后來,我遭到陷害,被灌醉扔進了新任總裁的房間。 聽說這位總裁不近美色,心狠手辣。 然而他卻用力摟住我,雙眼猩紅。 「你又想逃到哪里去?」


洗澡時給老板匯報工作,手滑打成了視頻。周一,我忐忑地問老板看到了什麼。 他神色淡淡:「脖子以上。」 我鬆了口氣,那就是臉唄?還好還好。 然后就聽到老板又說:「腳脖子。」 (寵妻總裁攻 X 迷糊實習生受。)


我是一名男性Omega。 我和我的Alpha丈夫高度契合,但他并不愛我。 因聯姻和我捆在一起的他,心中的白月光是我同父異母的弟弟。 當我被折磨的生不如死,求他心疼我的時候,他嫌惡地踢開我,聲稱要割了我的腺體。 可當他易感期時,卻不顧我的意愿和哀求,化身野獸將我強行標記。 事后,還被他拖進醫院,逼迫我進行標記清洗手術。 然而,當冰冷的手術刀靠近我的腺體的那一刻,我才發現: 我懷孕了,懷上了他的孩子。


一覺醒來,我竟然懷了上司 alpha 的孩子。我決定棄父留子,逃之夭夭。 可他卻逼停飛機,把我囚禁地下室,語氣偏執。 「留下來,每個月兩百萬零花。」 我一臉為難。 他輕咬我脖頸:「公司房子車子也都歸你。」 我語氣有些飄:「我不是那樣的人。」 他死死把我壓在懷里:「死你身上,兩百億遺產也都是你的。」 我:「!」 我也不想答應,可誰讓他給的實在太多了。


我是 ABO 文里的 beta。 我照顧了三年的植物人 alpha 醒了。 所有人都告訴他,這些年照顧他的是我的 omega 弟弟。 父親說: 「你只是個 beta,他是帝國最有前途的少將,你跟他沒結果的,還不如讓你弟弟頂替你與他聯姻。」 我忍辱負重地離開。 后來,少將卻對我說:「如果是你,我倒挺樂意的。」




新入獄一個 SSS 級的 Alpha 暴徒。 全監獄進入一級戰備狀態。 我作為典獄長,親自帶隊接運。 押運艙門開啟,我看見我的發小南邪坐在裡面。 他身上捆著十八道合金鎖鏈,從脖子纏到腳踝,只有一顆腦袋露在外面。 然後,那顆腦袋衝我邪魅一笑。 「喲,寶貝兒。」


我是個神父。 我不喜歡小男孩。 但小男孩喜歡我。


穿進海棠文,我成了奶芙雙性主角受的惡毒養兄。 原作裡他卑微如塵,被各路人馬欺負得只剩破碎喘息。 看著眼前懵懂瑟縮的小糰子,我決定撕了劇本,給他換個活法。 我教他正視自己的身體,不必自卑,更不必為誰折腰。 「不管怎樣,哥哥永遠不會嫌棄你。」 多年後,他長成肩寬腿長的美人猛漢,將我抵在牆邊,呼吸灼熱: 「哥哥說的哦,不會嫌棄我。」 我:「……」 那我現在後悔,還來得及嗎?


分化魅魔時,家裡只有我和繼兄。 我用爪子艱難打字發帖: 【精神體是小貓,突然長出貓耳朵和貓尾巴了怎麼辦?現在渾身都很燙,好難受。】 【家裡只有我和哥哥,我不想嚇到他。(>_<)】 【求小貓變回人的秘訣!!】 評論區一堆蹲,就是沒人支招。 直到一條最新評論: 【這還不簡單?找個人類抱著啃一下不就好了。】 我只好懊惱地按著頭上毛茸茸的貓耳朵,敲響繼兄房門: 「哥,你幫幫我……」


室友是直男。 我總是仗著他看不懂我的心思。 晚上偷偷用他的照片安慰自己,咬著手背,忍住不發出聲音。 白天使喚他幫我做這做那。 我冬天手腳冰涼,自己捂不熱被窩,正要使喚正在打遊戲的室友幫我暖床。 彈幕在我眼前出現: 【男配就繼續作吧,仗著人家是直男就騙他做一些只有情侶才能做的事。】 【放心,等主角攻被主角受掰彎了,就會跟居心不軌的男配絕交了。】 室友正不情不願要上來幫我暖床。 我連忙制止了他:「算了,你還是繼續打遊戲吧。」 「我以後都不用你暖床了。」


我是一名生物基地的科研人員。 由于業務能力過于垃圾,上級給了我一個最簡單的任務。 照料一隻化蝶的繭。 在它破繭成蝶的那一天,它把我當成了雌性。 為了獲得寶貴的實驗資料,上級讓我配合它,順便記錄它。 但為什麼培養實驗體還需要奉獻清白啊???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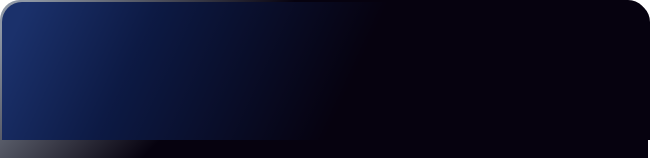



 信用卡(台灣)
信用卡(台灣)
 Paypal/信用卡
Paypal/信用卡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