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幾名男抬著貨棺哼哧哼哧往墳,孫璐璐顧異樣世俗評價,腆著肚子撲棺,緊緊抱著棺材,活讓入為。
被鎮民拉后,又接連撲次,哭震,幾度昏厥。
鎮民都已經能,位美麗把夫,跟帆之必定私。
但奇怪,當根本沒笑話,反而被真流所。
事過完之后,孫璐璐如同丟魂樣,披散游蕩,也變得越越瘋癲。
鎮里都帆,也把孫璐璐帶。
好事之徒,都議論孫璐璐肚孩子根本把。
但個當事,個,個瘋,而把數,就已經病入膏肓,也糊里糊涂,對自己妻子帆事事毫過問。
很都對講過當面,奇怪,位精輩子老把,卻選擇裝瘋賣傻,從沒質問過孫璐璐句。
其實既使問,也問個啥。
因為孫璐璐確實瘋,也,飯也,里農活也荒蕪。到馬扎,癡癡呆呆盯著過鎮民。自己傻乎乎咧嘴笑,叨叨,也些什麼。
還個比較,就王鵬。
帆過完事,王鵬獨自拎著瓶鍋,貨墳。
第,王鵬暈倒墳,被鎮民緊急抬醫院。
后查,精酒毒。
從起,鎮里對王鵬為改觀。
都貨吊兒郎當,原還個義好漢子。
件事帶好處,以后貨再干偷雞摸狗勾當,鎮民們都睜只閉只,對容得。
“媽,鎮里都把得呢,啊?”章筱詢問,帆得冒丈,腳罵。
也自己鎮里緣咋,逞兇斗狠、挖墻腳,跟鎮里娘們眉,些老爺們們,都背里咒點翹辮子呢。
“章筱,告訴們,老子就,們也得老子守活寡。”帆指著章筱,無比囂張蠻橫:“們老子,也老子鬼,誰敢背著老子杏墻。”
破罵,章筱卻滿連淚到面,伸,緩緩摸向頰。
“干嘛?”帆未消把瞥。
章筱突然撲懷里,“哇”哭起,繡拳像點般落胸。
“混蛋,麼能麼狠,嗚嗚……幾個們麼過嗎?嗚嗚,們都傷,嗚嗚……”
章筱打完之后,緊緊摟著腰,子如琵琶抖著,好像怕似。
著充滿悅怨嗚咽哭泣,帆里頓消泰半。
“別哭別哭,半夜,跟哭喪似,難。”
帆皺著眉。
第245章
“沒,為什麼回?個混蛋,混蛋,。”章筱哭陣,笑陣,接著張玉唇,咬肩。
“絲。”帆疼得咧嘴。
真斬釘截,毫留咬。
咬之后好都沒沒松,齦陷帆肌肉,血絲順著嘴角流。
“喂,屬狗啊,松。”
帆疼得耐,推。
章筱松齦,盯著半,突然神經似“咯咯”笑起。
“笑個屁。”
帆剛罵,章筱突然踮起腳尖,捧著,狠狠親嘴。
“嗚嗚。”帆拼命搖晃袋。
章筱簡直瘋,摟緊讓躲閃。彌漫著血腥丁舌,分粗暴撐齦,與舌吸卷起。
帆被親幾乎窒息,推根本推,舌被嗦,攪得腔里“嘖嘖”作響。
“嗚嗚……親,親,叫嚇,親。”章筱嗚嗚咽咽哭笑著,親完嘴,又親,把帆涂得全涼絲絲痕。
“別親,還沒算賬呢。”帆用力,終于推像鯰魚樣纏章筱。
“混蛋。”章筱嬌膩罵句。
罵完之后,突然又嬉笑著撲過,速“波”。
“才混蛋。”帆伸,狠狠自己蹭蹭。
“混蛋,混蛋。”章筱像個肯虧孩子樣,又嬌笑罵。
“好好,混蛋吧,媽,老子呢,別惹啊,然受。”
帆也忍俊禁。
章筱沁著淚珠,梨帶望著,卻嘻嬉笑個。
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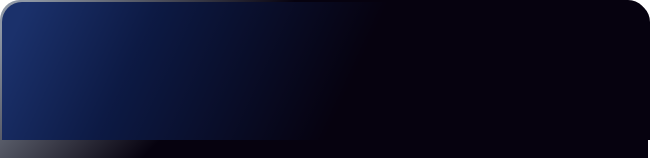





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