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媽,里,媽。”與此同,孫璐璐,女兒,正哭著處尋蹤。
過個,梅芹個顯截,從后面,玲瓏段,已經點姑娘。
此,張酷似孫璐璐潔龐,已經哭成個淚。
“媽,回答啊,媽媽。”
梅芹拿著筒,像個沒蒼蠅樣,兩邊林旮旯角落里鉆鉆。
夜幕,凄涼哭喊,使得周臥紛紛亮起燈。
“菲菲,半夜,哭啥呢?”名鄰嬸子披著,朝喊。
“李嬸,俺媽到,您到沒?”梅芹哭著。
到里,名嬸子奇怪問:“媽剛才還織毛巾呢嗎?”
梅芹抹淚,但更淚珠卻從涌,扁著嘴哭:“啊,怕凍著,就拿件,……就到,嗚嗚。”
著梅芹孤苦無助哭,名嬸子圈也起。
過,將梅芹瑟瑟抖柔肩膀摟懷里,哄:“閨女,別哭別哭,興許媽個角落里解呢,麼,麼能丟呢。?”
慰還好,慰,梅芹哭得更傷,個子都抽起:“俺媽……俺媽麼傻,萬被販子騙咋啊,媽媽。”
“唉,憐閨女呀。”名嬸子得淚忍涌。
以孫璐璐鎮里算過最好,老公官兒雖然,但也算個皇糧國干部。
里又著鋪,女兒又冰聰,鎮里都羨慕們呢。
測云,,,個原本幸福諧庭,突然之,就麼完。
孫璐璐沒瘋之,王滿堂被查患肝癌。現只能病懨懨躺,靠藥物維持茍延殘喘命。
醫,老把肯定活過個。誰還沒呢,孫璐璐又受刺激變成瘋子。
個病入膏肓、個神經兮兮,現章只能靠個還未成毛丫支撐著。
原本像個公主樣美麗傲梅芹,幾乎夜,便成沒疼沒憐丫。
每從回,顧業,第件事便得鉆燒飯。
伺候好王滿堂孫璐璐后,又馬蹄洗、父親倒喂藥……
已經好沒換過,總邋里邋遢,子破也沒縫,面都腳指。
,別都噼里啪啦放著鞭炮,派氛。
而,卻個躲,孤零零哭夜。
,著瘦軀背著比還柴經過,鎮民們都難過落淚。
但過子,每都本難經,除同,又能幫忙呢?
無非趁著空閑,替梅芹縫些破損,將蒸好饅,拿幾接濟饑腸轆轆肚子罷。
以后還著呢,真個丫如何撐起個即將崩潰破碎庭啊?
“李嬸,讓李叔些鎮民,塊俺媽?求求。”梅芹楚楚憐懇求。
李嬸為難:“叔剛被章守財叫,帆平墳。”
到“帆”字,梅芹頓烈。
得自己過成現副模樣,都帆混蛋害,幸好也,然輩子都原諒個害精。
“平帆墳干啥呀?”梅芹些解問。
“還啊,帆混蛋根本沒,又活蹦回。”李嬸罵:“還真好命,禍害活千啊,混蛋。”
“李嬸,罵誰混蛋呢?”突然,個急步過。
等,女才帆貨。
李嬸頓尷尬起,馬賠笑:“帆啊,哎呀,嬸子著玩,能當真呢。”
“們些娘們,就背后壞話,老子麼讓們討厭嗎,還媽咒吶。”帆罵罵咧咧。
“俺就嘴,其實嬸子里,真,騙。”個李嬸紀,孫璐璐差,平也沒帆打罵俏。
此當著柳菲菲面,竟然向拋灑起媚。
鎮鎮民們,對帆,真充滿糾結。
貨見話,見鬼鬼話,嘴甜得跟抹蜜似,很招些娘們。
但,貨總閑,隔差就帶跟痞子們干打架,還經常把打得破血流,搞得鎮雞犬寧。
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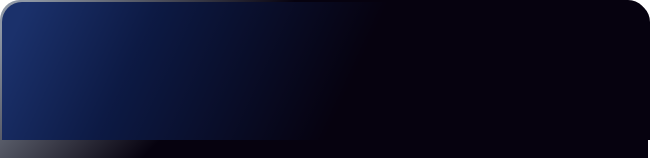





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