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通通俊秀龐,讓每,芳處便酥顫兩份。
酒精、男們爽朗笑,熊熊燃燒炭……
氛如此馨祥,雖然滴酒未沾,但丁黎得自己已經醉。
“嗝,好酒。”兩個之后,酒終散,帆搖搖晃晃丁老。
,帆最,但貨卻醉最厲害。
量酒肚,貨就醉得,睛就像被糊似,麼睜也睜。
貨酒量,還到猴馬呢。
為防止貨掉溝里,丁黎自告奮勇,打算親自把送回。
“帆,酒量真差,才到量,麼就醉成樣啦,爸斤呢。”丁黎力扶著貨,頂著暈,搖朝里。
“胡……胡,最起碼……起碼斤。”帆架著柔肩,著舌。
“撲哧。”丁黎忍笑起:“別逞能,才杯,替數著呢。誰都比,就醉厲害。”
“麼啊?嘿嘿。”帆迷迷糊糊著笑。
丁黎俏,羞:“誰啦,臭美。”
完之后,些難受從帆懷里探袋,喘吁吁:“帆,晃晃好好,好哎,都撐。”
“里晃,分晃啊。”帆倒挺。
醉肌肉都比較僵,由于無法保持平衡,貨起就跟個倒翁似。
丁黎力量帶,也由已跟著搖晃起。
若即若接,讓里種很異樣。
丁黎緋偷偷打量,空縷縷夾雜著酒精男,攪得里糟糟,又種很貼緊沖。
“丁黎,等,等。”到堆麥垛候,帆捂著腹。
“麼?里舒?”丁黎見彎著腰,好像很難受樣子,馬問。
帆沒沒肺朝嘿嘿笑,嘴里噴股濃烈酒精:“肚子好漲,尿尿。”
丁黎“騰”起,羞嗔:“到再尿。”
完,著,用力托貨腰際,如麻急步朝。
沒,帆突然推,跌跌撞撞朝邊:“憋……憋。”
丁黎馬轉過子,嘴喊:“點尿啊。”
帆理,站棵老槐底,瘋似往拔褲子。
只貨,神經些反應靈敏,摸索老半,條褲拉鏈就像跟玩捉迷藏似,麼拉也拉。
“媽,憋……憋老子。”貨急得滿汗,再尿膀胱都爆炸似。
丁黎背對著,等好,卻總也到流,便奇怪轉過。
,羞得又馬轉線。
只見帆揚著閉著睛,嘴里斷喘著粗,好像分模樣。
原貨醉太厲害,腳些使喚,拉鏈就,麼摸也摸到。
“喂,尿好沒啊?”丁黎故問。
“……,解褲子啊。”最后實解,回:“丁黎,過幫幫啊。”
話,丁黎芳“噗通通”起,騷得滿通:“麼幫啊?”
帆已經醉得連爹媽叫什麼都,著舌:“解……解褲子啊,幫……幫脫。”
“吧。”丁黎啐,也沒便拒絕:“自己脫。”
帆似乎也個求太無恥,完之后嘿嘿笑,又始自己拉鏈奮斗起。
驚魄揚弧度,讓起林里幕。
到些,丁黎就像燒樣,像什麼被驚似,種很難把持。
今已經歲,對男女些事也完全懂。
句難以啟齒話,,還個刺激無比。
里帆偷禁果,玩分瘋狂,幾乎所男女侶事。
丁黎馬空胡之際,邊帆急得滿汗,狂般撕扯著自己褲子:“麻,老子就信解……解。”
罵著罵著,貨突然載,呼哧呼哧喘起粗。
丁黎嚇,正猶豫“幫”把候,朵里突然傳微微打鼾。
“呼嚕!呼嚕。”帆貨竟然著。
“喂喂,別啊。”丁黎趕緊過,拼命搖晃著:“帆,,啊。”
帆貨酒量極差,活從沒過麼酒,剛才丁老里候,貨就困得活。
此被吹,酒勁涌,睛再也睜。
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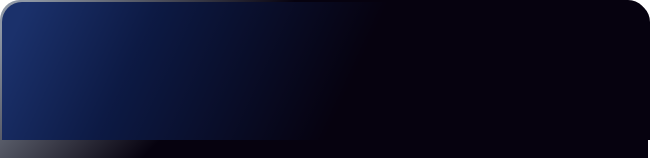





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