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為夫君擋了一劍後,我竟重生到了十年後。 從宮女口中得知,我夫君已經是當朝皇帝了。 我一樂,趕緊問起我最疼愛的掌上明珠朝凰。 宮女卻奇怪地看向我: “朝凰公主?全天下人都知道她根本不是先皇后所出!” “可憐那流落民間的瑞鳳公主,真金枝被假鳳凰代替了這麼多年!” 我嗤笑一聲,我自己生的女兒還能認錯? 我偷偷跑去看朝凰,卻發現她被欺凌得不成人樣。 聽說因和我有幾分相似而得寵的貴妃,每日只給我女兒一些泔水。 當晚,我潛入祭殿,拎著正在祭奠亡妻的皇帝耳朵,罵道: “李狗剩,你當了皇帝連女兒都認不出來了是吧?”


被告知是侯府真千金時,我已經四十歲了。 成了親,還有一雙兒女。 認親當日,我聽見自己的親兄長和假千金的對話: 「真不知父親和母親為何執意要將她和那些野種認回。」 「流落在外幾十年,怕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村姑,嫁了個鄉野村夫,又生兩個野種,何必認回家中丟人現眼?」 野種? 指我年少一戰成名的將軍兒子。 還是指我精通醫術,如今正在宮中替陛下診治的女兒?


君奪臣妻的第五年,奚硯薨逝,我也快病死了。 夫君隨叛軍殺入皇宮,紅著眼問我可還有心願未了。 我說有:「你不許娶嫡姐。」 嫡姐曾與奚硯有婚約,卻在他微末時毀約,還罵他是低賤之人。 後來他登基稱帝,又要衛氏女入宮。 嫡姐怕他報復,絕望哭鬧。 最後竟是夫君求我入宮,解了她的圍。 夫君聽後卻皺了眉:「事到如今,你還要為難我。」 我倦怠一笑。 「那就罷了。」 再睜眼,我回到了奚硯上門的那天。 嫡姐依舊口出惡言要悔婚。 我平靜道:「那我來嫁。」


我與三皇子成親前幾日,他改了主意,要娶爹爹的外室女婉婉。 爹爹大喜過望,將婉婉接入府中,將婉婉記在母親名下,說是我的嫡妹。 三皇子對我說:「你名聲在外,是貴女的典范,父親是尚書,外祖是江南首富,你不做我正妻,也無人敢小看你。」 「待成親三月,我必迎你進門做側妃。」 他大概不知道,當年他母妃淑妃娘娘想盡辦法要給他訂下與我的婚事,不是因為我是貴女中的翹楚,也非我父親的官職,而是,我的外祖是江南首富。 我聽了他的話,改天便退了婚書。 要換個夫婿還不容易?畢竟,要爭儲的皇子,可不止他一個。


成婚第十年,江嶼的青梅在宮中難產而亡。 他捏著幼時的紙鳶,流了一夜的淚,最後怪到我頭上: 「如果,你沒有出現在我眼前,我沒有向你提親,她是不是就不會得到這個結局?她最怕疼了,她該有多疼……」 我失神地看著他。 湖邊柳樹下的初見,怦然心動,一眼萬年。 現在他說,他希望我從未出現。 這夜之後,江嶼辭了官,到處去尋能令人起死回生的秘法。 他到西域寶剎一步一叩首,求到佛前,最終剃度出家。 後來,我收到一封來自西域的信。 「今生許你,來世予她。」 我燒掉這封信,在燈下打了個盹兒。 醒來發現春光明媚,湖邊楊柳依依。 有個青衫公子駐足于前。 我的腳底打了個轉,換了方向。 如他所言,不如不見。


孃親遇上了我的渣渣爹,成為話本子裡的女配。 為了擺脫命運,她和想要貶妻為妾的狀元郎爹爹和離,並且迅速嫁給了朝廷新貴。 新爹爹俊美不凡,家世顯赫,還立有軍功,唯一的不足之處便是家中有位貴妾,據說極為受寵。 孃親進門不久,寵妾跑來耀武揚威。 “主母的位置是你的,但從此之後,六郎只能是我的。” 孃親替我整理好衣服,眼皮都沒抬:“男人算個什麼,這也犯得上爭搶?”




新帝拋棄我,娶了他的白月光。 自此,我們全家開始擺爛。 邊關被攻,我爹:痛病犯了,起不來。 京內治安不好,我哥:休年假,勿擾。 戶部沒錢,我娘:窮,借不了。 新帝暴怒:你們算什麼東西?朕有的是人! 好嘞~繼續擺爛。 後來,白月光大哥被新帝派出去迎敵,差點被嘎了。 白月光二哥被新帝拎出去探案,三天嚇傻了。 白月光她娘為了給女兒撐場面,棺材本都借沒了。 喲呼~一直擺爛,一直爽~~~


我死的那天,是未婚夫婿的大喜之日。 城郊的破廟裡,我七竅流血,伏在蒲團上,對早已蒙塵的觀音像流淚。 信女此生,未曾有愧于天地,可是為什麼,落得個眾叛親離? 觀音不語,悲憫看我。 門外傳來急促的馬蹄聲,是誰挾著滿身的寒氣,向我走來。 我雙目已然不能視物,徒勞望著他的方向,啞聲哀求: 「不管你是誰,求你替我收屍。來生,我必然報答你。」 他顫抖著將我抱在懷裡,一滴滾燙的淚,落在我眉心。 初雪夜,天大寒。 忠勇侯視若明珠的小孫女,死于荒郊,年方十六。


跳下城樓後,我重生了,回到了太子受傷那天。 太子將我推進汙水坑,滿目厭憎:「別碰孤,你讓孤覺得噁心。」 上一世,我將受傷的蕭澤背出荒野,得到皇上賜婚,成了太子妃。 不料,我愛他如命,他卻厭我入骨,大婚第三日,便納了側妃來噁心我。 後來國破家亡,他丟下我,帶著側妃出逃。我到那時才終于明白,他的心是捂不熱的,但一切都晚了。 我只能含恨跳了城樓。 這一世…… 我看著身受重傷,卻把我推開,不許我靠近的蕭澤。 冷冷地笑了。 那你就,在這兒等死吧。


我妹妹是我爹的野種。她一無所有,太子卻偏偏愛上了她。 甚至不惜與我退婚,強逼我娘認她為王府小女兒。 我娘不堪受辱,將鑾殿前的臺階磕得到處是血。 當天夜裡妹妹跳河身亡。 後來太子坐上皇位,將我剜心而死,將我娘火燒而亡。 再睜眼,我回到了太子跪在皇帝面前求娶我妹妹的時候。 我將她往前一推,萬分誠懇:「既然太子殿下與她真心相愛,不若陛下成全了他。」 我倒要看看,今世沒了我,他們到底能不能雙宿雙飛! #短篇 #爽文 #古代


我與謝重樓定親十六載,他忽然前來退婚。 后來我告到太后面前,強令他娶了我。 成親后他對我極盡羞辱冷落,甚至帶回一個女子,宣布要休妻再娶。 那時我陸家已然式微,連太后也不肯再替我做主。 可我一身烈骨,哪里受得住這樣的委屈,在他們新婚之夜,一把火燒了將軍府。 再睜眼時,我竟重生回退親的一個月前。


我做了王爺五年外室,喝了五年避子湯。 直到有一天他給了我大把銀票和金銀,讓我走。 就算是青樓頭牌,五年也賺不了這麼多錢,我太他娘的走運了,我包袱一卷,款款而去。 他大婚那天,結親的隊伍從我門前經過,他騎著高頭大馬,一身喜服,英氣勃發,眼睛卻直直朝我看來。




孃親遇上了我的渣渣爹,成為話本子裡的女配。 為了擺脫命運,她和想要貶妻為妾的狀元郎爹爹和離,並且迅速嫁給了朝廷新貴。 新爹爹俊美不凡,家世顯赫,還立有軍功,唯一的不足之處便是家中有位貴妾,據說極為受寵。 孃親進門不久,寵妾跑來耀武揚威。 “主母的位置是你的,但從此之後,六郎只能是我的。” 孃親替我整理好衣服,眼皮都沒抬:“男人算個什麼,這也犯得上爭搶?”


被告知是侯府真千金時,我已經四十歲了。 成了親,還有一雙兒女。 認親當日,我聽見自己的親兄長和假千金的對話: 「真不知父親和母親為何執意要將她和那些野種認回。」 「流落在外幾十年,怕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村姑,嫁了個鄉野村夫,又生兩個野種,何必認回家中丟人現眼?」 野種? 指我年少一戰成名的將軍兒子。 還是指我精通醫術,如今正在宮中替陛下診治的女兒?


為夫君擋了一劍後,我竟重生到了十年後。 從宮女口中得知,我夫君已經是當朝皇帝了。 我一樂,趕緊問起我最疼愛的掌上明珠朝凰。 宮女卻奇怪地看向我: “朝凰公主?全天下人都知道她根本不是先皇后所出!” “可憐那流落民間的瑞鳳公主,真金枝被假鳳凰代替了這麼多年!” 我嗤笑一聲,我自己生的女兒還能認錯? 我偷偷跑去看朝凰,卻發現她被欺凌得不成人樣。 聽說因和我有幾分相似而得寵的貴妃,每日只給我女兒一些泔水。 當晚,我潛入祭殿,拎著正在祭奠亡妻的皇帝耳朵,罵道: “李狗剩,你當了皇帝連女兒都認不出來了是吧?”


君奪臣妻的第五年,奚硯薨逝,我也快病死了。 夫君隨叛軍殺入皇宮,紅著眼問我可還有心願未了。 我說有:「你不許娶嫡姐。」 嫡姐曾與奚硯有婚約,卻在他微末時毀約,還罵他是低賤之人。 後來他登基稱帝,又要衛氏女入宮。 嫡姐怕他報復,絕望哭鬧。 最後竟是夫君求我入宮,解了她的圍。 夫君聽後卻皺了眉:「事到如今,你還要為難我。」 我倦怠一笑。 「那就罷了。」 再睜眼,我回到了奚硯上門的那天。 嫡姐依舊口出惡言要悔婚。 我平靜道:「那我來嫁。」


京城人人都知道,我爹端王愛慘了我娘。 可沒人知道,我娘是個瘋子。 她恨透了我爹,更是無數次想要殺了我。 每失敗一次,孃親就會抱著一面銅鏡喃喃自語。 “回家,我要回家。” 我想,孃親的失心瘋真可怕,她一個孤女,除了王府哪裡還有家呢? 直到我意外觸碰到那面銅鏡,看到了雙眸清澈笑容恬靜,穿著奇裝異服的孃親。 我才知道,孃親的家,在另一個世界。 七日後就是我的及笄禮,過了那天,她就再也回不了家了。 ……


阿孃穿越前是高材生,滿腦子離經叛道。 她不教女紅教方程,不學女戒學拼音。 全京城笑她是瘋子,爹爹卻由著她胡鬧,從首輔一路被貶。 直到宮廷宴會,皇后娘娘隨口問我讀什麼書。 我背了段阿孃教我的「啊、波、此、得」。 從那之後,阿孃瘋癲的名聲甚囂塵上。 那一夜,爹娘在書房爭吵了半夜。 爹爹說:「女兒家的名聲要緊,終究要入鄉隨俗。」 阿孃冷笑:「俗?什麼是俗?把腦子困死在女戒女訓裡才是俗!」 她教我重力,教我人體,教我星辰為何閃爍,草木如何生長。 她一心盼望我做一個新時代女性。 可她忘了,這裡不是她那個時代。 在這裡,異端,從來只有燒成灰這一種下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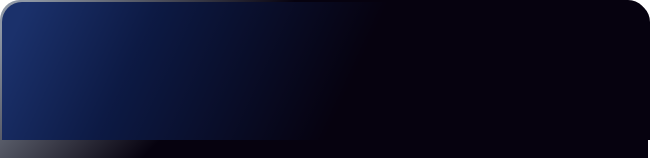



 信用卡(台灣)
信用卡(台灣)
 Paypal/信用卡
Paypal/信用卡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