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賴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汶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張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葉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我要加入
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{{item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不限
支持
不限
0-2w
2-5W
5-10W
10W+
不限
VIP
免费

柳承而后對爺爺,“您麼起麼?”
爺爺回答,“里麼事兒,兒能得,孫清爹娘還子里躺著呢。”
柳承簡應,然后轉對,“跟趟。”
柳承著也管爺爺,徑直,雖柳承什麼,但于對信任親昵,也直接跨跟,爺爺直背后著們,等們截兒后,爺爺突然沖們喊,“柳師傅。”
柳承腳步回爺爺,“恩?”
爺爺猶猶豫豫,像什麼難言之隱,好兒才,“柳師傅,今兒能?”
柳承微微笑,,“為什麼?”
爺爺嘆,哆哆嗦嗦取煙槍叼嘴里,也點燃,就吧嗒吧嗒抽起,而后對柳承,“候,見狐貍腳印,致也已經,當只報喪狐貍問題,但畢竟系到孫清娘,些孫也算兢兢業業,所以把狐貍腳印抹,著柳師傅能能睜只閉只,放。”
爺爺完,柳承猶豫好兒,然后爺爺禮鞠躬,“孫清份,只沒過什麼傷害理事,盡量對。”
“造孽喲。”爺爺像瞬老歲,本就陷眶里竟然擠幾滴淚。
個自己招兒媳婦兒問題,自己又被隱瞞麼,爺爺必最痛吧,保全庭,又完成當老神使命,才最為難個。
爺爺已經娘問題,柳承繼續查,遲把矛指到娘,只能求柳承能睜只閉只。
柳承帶著,沒即娘,而帶著墳塋,到自己墳站兒,又從墳墓旁邊洞里掏盒子,打盒子,里面裝件干干凈凈袍,還把晃晃劍,袍劍旁邊,擱置個鬼面面具。
柳承著袍法劍,像未見老朋友樣,滿熾懷,端里好久,而后摸摸們,,“老伙計,又該用們。”
柳承著將袍穿,著柳承怔怔語,穿袍跟平完全樣,平常笑容,兒確實股子拒千里之質,就跟里神像樣,雖然也笑盈盈,但總同。
柳承隨后把盒子好又塞墳墓,才句,“墳墓太爛,別話,肯定就能把劍袍拿,等忙完幫修修。”
柳承著笑笑,再,“世還沒誰敢掀墳墓,即便棺材曝于荒野,牛鬼蛇神也繞而,過孝,過幾以把棺材挖曬曬太陽,讓本什麼樣子。”
額,只得后背涼,搖搖,“還算,麼,尸💀肯定爛成骨。”
柳承笑而語,把鬼面面具交,而后從袍里取張表,伸指對著表劃幾,再松表,句‘敕’,完也兒突然陣,卷著表。
處,見只們塊兒,們塊兒,面皆,只得神奇無比。
柳承,“吧,只狐貍。”
于柳承跟著表起,表漸漸,們跟隨,很就們附幾個子,入老林。
方叫‘崖’,以里個煤礦,里都里挖過煤炭,因為距方比較,們之后能當回,所以就崖邊兒修臨所,最始還好,但久就現,當初被攆些豺狼虎豹全都聚集崖里。
里們最后容之所,些野獸無退,于兩成群結隊現,圍著當挖煤炭所吼叫,久而久之,也怕,就崖,敢再踏里半步。
方也只爺爺過,從沒過,柳承卻直接帶著里,讓些緊張,怕些猛獸還邊兒沒。
崖幾跡罕至,原本們辟也被荊棘叢擋,們得極其困難,或許理作用,跨崖,就直背后盯著們,但屢次回,卻見后。
,將兩個,直到靠崖當初個煤礦候,柳承轉過對,“把面具帶。”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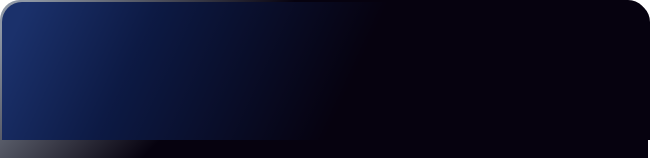



 信用卡(台灣)
信用卡(台灣)
 Paypal/信用卡
Paypal/信用卡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