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賴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汶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張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葉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我要加入
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{{item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不限
支持
不限
0-2w
2-5W
5-10W
10W+
不限
VIP
免费

柳承微微笑笑,卻笑得跟致命神般恐怖,令悸,而后,“以為就治們?”
“敢敢。”劉仁通連忙叩首回答。
柳承又瞥跪旁邊張猛等,旋即再,“養群,再奉先,餓鬼,狗彘,就治理奉先?”
張猛等話,得柳承處理們,抬,滿恐懼。
劉仁通再雞啄米似點,“今后定兢兢業業。”罷回令,“把張猛、林幕府全帶回候處置,今參與差全都剝資格,淪為普通游魂。”
柳承笑笑,再搖搖,“倒用,千差怕個隍廟底,把們都處理掉,今后誰還管理陽游魂野鬼?”
“全您,您麼,全都照辦。”劉仁通。
柳承旁邊爺,對招招,“過。”
爺站起邁步過,到柳承旁邊拱禮,柳承問劉仁通,“認識嗎?”
劉仁通,“認識認識,張司殿提攜。”
柳承恩,“得錯,事剛正阿,善惡分,以職權壓,該麼嗎?”
劉仁通幾秒,再,“張猛貶為普通鬼魂,坪取而代之,執掌隍印,居隍廟。林幕府貶為普通游魂,孫清隍廟幕府。”完再試探問柳承,“您樣?”
柳承笑笑,“以,張猛、林幕府都岳帝,個面子,今放們馬,親自審問們,犯什麼錯,什麼事,全都審清楚之后再秉公辦事。”
罷再向跪旁理誠,劉仁通也瞧見柳承目,連忙,“,們好管……您……”
柳承站起對劉仁通,“帶著滾蛋。”
劉仁通連忙應,而后帶著些差呼呼啦啦,還趔趔趄趄步晃,顯然剛才被嚇得。
們都之后,里就剩理誠個,理誠咽著唾沫著朝過柳承,也敢也敢,等柳承到面后,柳承著微微笑,“帶嗎?陳瑩瑩就里,本事帶。”
什麼玩笑,當著帝面帶,嗎。之理誠只以為柳承教輩分比較,現終于,柳承面比劃本事,根本就班弄斧,自討苦。
“師祖……”理誠。
還沒得及求饒,柳承就打斷,對著旁邊蘊招招,“丫過。”
怕也只柳承敢麼稱呼蘊,蘊邁步過,眨巴著著柳承,柳承,“把挫骨,再對布煞鎖魂陣?”
蘊恩。
柳承又,“現交,麼對,就以麼對。”
理誠對事太過喪病狂,如果直接打得魂魄散還好,什麼都到,什麼也到,偏偏把蘊挫骨之后,還用惡毒陣法把鎖幾,沒親起驗過,永也其痛苦。
理誠麼對蘊,現蘊以報仇,但卻猶豫,被鎖幾,什麼受,正所謂相由,蘊就種錙銖必較,又麼能得樣事,于著柳承搖搖,“。”
柳承皺眉,“被欺負得麼慘,就報仇?”
蘊,“全真,麼對話,萬全真們麻煩麼辦。”
蘊自己麼對理誠,只能搬全真事兒,柳承也蘊狠,也勉,站旁邊戰戰兢兢理誠,“把劍拿起,跟比劃,如果次之后還沒,則,放馬,如果活,命該絕。”
剛才已經跟柳承比劃次,就已經招致,再次話,只次劈,怕就被當劈,理誠當就愣,種事兒,連連搖,再跪叩首,“錯。”
柳承見求饒,卻彎腰把把提起,碩個兒,柳承里卻變得無縛雞之力,像個連放屁都扶墻似,柳承直,“愿比,就自己試試被挫骨鎖魂滋,個數,再比劃,就別怪客。”
趕鴨子架,理誠認命,等柳承松后,到旁拿起法劍,次再舉過頂,而放腹部位置搖起,姿態比本般還。
柳承漠然著,搖完后馬抬,只得嗤啦,弧劃破際,直接朝邊落,理誠拔腿就,到旁邊顆梧桐,正好落梧桐。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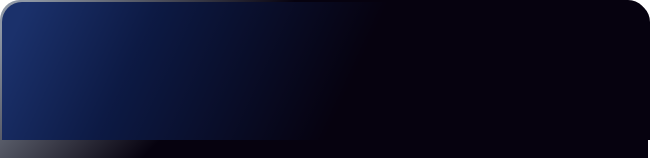



 信用卡(台灣)
信用卡(台灣)
 Paypal/信用卡
Paypal/信用卡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