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賴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汶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張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葉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我要加入
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{{item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不限
支持
不限
0-2w
2-5W
5-10W
10W+
不限
VIP
免费

著話愣兒,倒對孫仁話所,只麼,些太舒,就,“更峰攀登,又麼執著于司當對打壓?”
柳承完成并推翻司,而個制定兩千計劃,所以孫仁所把們當成報復司子,得并成。
隨后又添加句,“師父玩笑,應該只跟您玩笑,并真把您師父拉。”
以為孫仁因為柳承拉師父,才跟些。
完,孫仁卻盯著,緊皺著眉,很,“里,就樣個斤斤計較麼?即便今跟些,也準備跟。跟講些原因,跟拉完全沒系。”
“您懷疑師父,總得個理由吧。”
孫仁,“師父曾經陽兩界站最巔峰,們樣里,個世界都們玩物,拜樣為師孫福,但也定什麼候,就向伸獠,跟樣打交,必須得玲瓏,才能保證受其害。”
“也您猜測。”打斷話。
孫仁見實愿相信話,只得,“龍膽已經沒。”
“啊?”話鋒突轉,沒能反應過。
孫仁,“受傷之后,龍膽就消失見,被奪。另,袁守并真暈過,裝暈,因為該事。”
正處驚愕,孫仁又繼續,“以師父本事,都現龍膽見,又麼能沒現?敢確定已經龍膽消失事,卻言,其必蹊蹺。”
著只得暈轉向,肯定什麼,只忘記而已,卻沒到連龍膽都沒。
“您麼袁守裝暈?”問。
孫仁,“檢查過袁守吐鮮血,并血,而舌尖血。咬破舌尖,吐鮮血營造自己暈倒假象。”
起事兒,起孫仁蹲直檢查灘血事,原麼個原因。
“為什麼麼?”
“連都敢事世并沒幾件,除非能力者參與,而淇縣最能就師父帝辛,過個候帝辛根本沒,師父剛好幾,所以袁守算事極能跟師父。而算被何所害,卻算到師父,應該能什麼,害跟師父,所以才算到起。”
已經搖還點。
孫仁又繼續,“袁守算,以選擇,偏偏用裝暈種段,能到理由只為求自保才裝暈。如果里,師父個善之,即便柳承秘密,也至于裝暈選擇自保,見認為柳承因為個秘密滅,所以才裝暈。”
著子得很,回起跟柳承經歷種種,任何排候,都問愿愿,只得到回答后才施,利用,但相信害。
兒對孫仁,“還選擇相信,您也直祖……”
孫仁得回答,神篤定對,“如果現害,絕對睜睜著孫代血付諸流。”
第229章 文王吐子
孫仁很嚴肅很認真件事,表帶半點玩笑,也得嚴肅回答,“如果真話,站邊,過能永。”
態度,孫仁穩腳步幾,而后面若桃笑笑,伸搭肩膀,“自己判斷能力,被蒙蔽雙,凡留個,諸事妄言妄信。因為孫子弟,孫自己脊梁信仰,能成為任何附屬品。”話攬著肩膀往幾步,“起跟見面麼久,還什麼都沒送過呢,難怪跟些疏,師父事就暫且先談,免得傷們祖孫,什麼,幫買。”
最始見孫仁候,認為個脾很古怪,且很奸詐。但隨著接,逐漸現過刀子嘴豆腐。雖然嘴叫老祖宗,但里卻從沒把當成過老祖宗,只個姐姐而已。
孫仁過歲太,因常里修,著飾也都保持古制,數都以襲漢示,自然能吸引目。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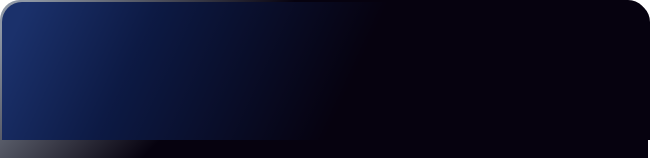



 信用卡(台灣)
信用卡(台灣)
 Paypal/信用卡
Paypal/信用卡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