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賴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汶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張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葉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我要加入
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{{item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不限
支持
不限
0-2w
2-5W
5-10W
10W+
不限
VIP
免费

至,忽見從滑落,將們圍堵兩之,后皆攔,退無,詔獄士見狀驚,忙聚攏將圍,,“埋伏,指揮使勿慌。”
們抽刀環周,忽得咻咻,翎箭襲,詔獄士連忙應對,過們本事微末,速度跟箭速度,久都負傷,箭法術力量,但凡箭刺過,都們留洞,很失戰斗力。
就、玄姬、玄雅還騎馬然無恙,詔獄士見能阻擋,對喊,“指揮使請馬,們拖們。”
“們連敵兒都,麼拖們?”淡淡,而后馬周圍,將目鎖定后方,彎腰撿起幾支箭,描淡將箭拋,,傳慘叫,隨后便轟鳴傳。
緊隨著就消散魂魄,頓,詔獄些士都愣,們此只以為靠跟岳系才當指揮使,沒到竟本事,個個目瞪呆。
倒,“還能話,就先。”
詔獄士蠕嘴角,本點什麼,卻沒,只得換,“方才些到底什麼,指揮使為什麼抓個舌問問?”
,“詔獄正盛,再加殺位判官,害怕,報復,管們什麼,只敢,都照單全收。”
猜都用猜,些個平等王,還般,而法術方士,過敢刺殺到,或許能成功,現刺殺,除非能請得玄女。
只個插曲,很稀松平常事,但些詔獄士里卻事,此后,紛紛,“指揮使得眉清目秀,們本以為指揮使法術,沒到竟般厲害。”
,“剛。”
“咱們副指揮使丁冥法術也極為得,詔獄兄弟,副指揮使陽跟提刑總司現任總教切磋過,招之就打敗提刑總司總教,指揮使副指揮使樣鎮詔獄,詔獄定然無憂。”詔獄士。
直沒管丁冥事,,鄭鈞提刑總司里,就算岳,都定能得鄭鈞,更遑論個副指揮使,們提起,才問句,“丁冥陽況麼樣?”
士,“具也清楚,過詔獄位兄弟從陽回,告訴副指揮使已經跟鄭鈞成為好朋友,副指揮使什麼,處置鄭鈞嗎?”
著愣,怕刀,就怕暗箭,丁冥跟鄭鈞成為朋友,個很危險信號。
袁守鄭鈞算過命,把鄭鈞結局告訴,以沒麼,現竟些緊張,鄭鈞斗得過丁冥麼?
岳把鄭鈞交丁冥,好插,現況插,量起對策。
讓詔獄士先回詔獄,回自己府邸,子后,玄姬玄雅變為本面目,問,“陸現什麼?”
玄姬先,“陸宗祠,陸第位老祖叫陸川,正當今司平等王名字。”
又向玄雅,玄雅,“陸老居方,里幾個燭殘老,觀面貌都已經百歲往,個陸子弟打,陸第個女兩世,但當個被張仁德父親抓起紈绔子弟還,叫陸洲,見,已經神志清,但問及祖父誰,咬定平等王陸川。”
“沒留什麼痕跡吧?”。
女搖搖,“都以魅惑之術探,們什麼都記得。”
恩,起,“跟平等王府。”
玄姬玄雅詫異,“現就,打驚蛇嗎?”
“就打驚蛇。”。
而后著簡裝,未帶任何兵刃,只帶變面貌玄姬玄雅,騎馬至平等王府,因為太,候平等王府已經閉,玄姬扣,許久才。
麼還被打擾,平等王府丁也頗為憤,沖沖,但見,頓愣,當呆,而后躬,“參見指揮使。”
旁邊個丁更忙通平等王,而個丁雖然參拜,但卻擋著讓,,“準備讓麼?”
丁忙叩首,“敢,只因平等王已經歇息,還請指揮使再。”
呵呵笑,也管丁,徑直就往子里面,邊邊,“平等王交代們讓府吧?此次連正裝都沒穿,并非為公務而,只跟平等王談談。”
正話,得府傳笑,平等王迎過,哈哈笑,“誰呢,原指揮使,丁懂禮數,還請勿怪,客堂敘。”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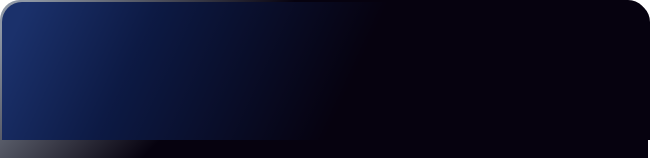



 信用卡(台灣)
信用卡(台灣)
 Paypal/信用卡
Paypal/信用卡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