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賴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汶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張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葉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我要加入
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{{item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不限
支持
不限
0-2w
2-5W
5-10W
10W+
不限
VIP
免费

半空,回,哥們位,目從面穿過,森森盯著。
神讓點自,于收回,目落飾品。
也為什麼,就瞬,里刷就現個怪異。
通袋,滿毛,兩米,居然還只獨角!
個像也就秒,然后就淡化消失。
但里卻震驚得很,再次個飾品,然后回問。
“,什麼?”
哥們著,倒沒回避,淡淡回句。
“犀牛骨,辟邪。”
犀牛骨,倒符剛才見像,起點犀牛樣子。
犀牛什麼候,袋還毛?
沒再繼續問什麼,反正玩跟也沒系,事如事吧。
于就轉,跟梁子起驗驗貨什麼。
結果到梯拐角,又現靠墻展示柜面,擺著個造型奇怪。
個展示柜概兩米,面還掛廣告牌,梯側也貼廣告,正常況見柜子面。
過梯個廣告牌剛好松,個縫隙,過候,就識往里瞄,結果就到柜子好像個物。
始以為里養貓,但仔細對,好像個蛤蟆!
幾就對蛤蟆比較敏,再加剛才哥們鬼鬼祟祟,就拿,打筒,速往里面照。
結果現,里面個圓盤,面趴著個蛤蟆……或者蟾。
蟾周圍擺著些奇奇怪怪,也沒清啥,只到蟾頂著抹暗。
但候沒再,因為已經傳腳步,哥們好像察到,!
趕緊掉,收回目,步梯,到梁子旁邊,然后回個廣告牌。
剛才蟾就擺廣告牌后面,正對著。
哥們已經到,懶繞過個展示柜,后面廁所。
過,過候,無瞥,個目里敵很顯,似乎告訴:別管閑事!
而且,過收臺候,還對員妹子句:“文文,梯廣告牌松,抽空弄。”
“好嘞哥,用抽空,馬就弄。”
個叫文文妹子爽應,起就處理。
個名字……讓稍微點恍惚,于就兩。
雖然此文文非彼文文,倒還幾分相似,個也差。
同張文文性格順,滿柔,個文文也睛雙皮,但舉止作很麻利,話也干脆利索,用句話:就“透溜”。
著子廁所,忍捅捅張胖,問:“哥們啥候,麼怪怪?”
張胖神變得些復雜,對們招招,示們話。
到,張胖拿盒煙分,點著抽兩,又里,才跟:“派麼?”
頓愣,點:“過。”
當然告訴,當們還跟個派老逼斗過法,打稀里嘩啦,為此還差點馬云峰送孕育醫院……
張胖往里努努嘴:“哥們據就派。”
頗為解啊,因為派,般社都極力掩飾自己份,個咋主往啊?
梁子也挺驚訝,問:“派,里邪派麼,真啊?”
張胖:“真假就,反正自己麼。”
也納悶問:“無,還告訴?”
張胖:“自己啊,公司里都,沒子擺些,著就挺邪性,沒事都。但劉總……”
到,沒繼續,過猜,笑:“劉總應該讓里布過局,吧?”
張胖:“沒錯,過也挺神奇,弄完之后,公司比以好,過也幾次事。”
問:“都什麼事?”
張胖:“先尚姐辭職,段自己總噩,班也迷迷糊糊,次梯候腳踩空,骨裂,回休養。”
“然后就崔,最猛,直接🏢,腿都骨折,然后也辭職。”
“還司哥,送貨跟打架,梁讓打斷,現還醫院里躺著。”
“還原里臺王,公司剛資,班就丟,沿半沒到,結果碰條野狗,被咬滿都傷,現還打官司呢,班也。”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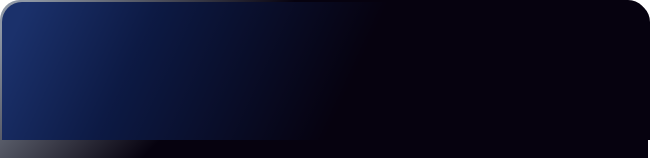



 信用卡(台灣)
信用卡(台灣)
 Paypal/信用卡
Paypal/信用卡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